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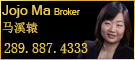 |
 |
 |
 |
 |
 |
 |
 |
 |
| 【本网讯】亨伯河医院(Humber River Hospital)重症监护病房的大厅里安静得可怕,除了许多病人的监护仪发出的哔哔声和振铃声。 没有家庭成员来访,因为他们要么在家中隔离,要么感染了COVID-19,无法前来看望他们的亲人。 每个病房外面都坐着一名重症护理护士,几乎像一名保安一样在值班。 关心是恒定的,也是复杂的。 今天,重症护理护士劳拉·梅林(Laura Mailling)正在护理一位40多岁的COVID-19患者。 “他正在使用我们能给他接上的最大剂量设置的呼吸机进行呼吸,百分之百的氧气。因为我们给他开了其他的药,所以他的血压也不稳定。他很年轻,但病得很重。” 梅林将把她的工作集中在这一位病人身上。 “我们给他们注射镇定剂,我们必须控制他们的血压。只有在重症监护室才能给病人开这种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门的培训来应对这一切。” 这些变化令人疲惫不堪,病例数量有时让人感到绝望,因为尽管团队尽了最大努力,一些重症COVID-19患者仍无法存活。 有时,他们会在只有护士陪伴的情况下死去,比如劳拉·梅林(Laura Mailling)。 “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我的病人非常年轻,40多岁,她死于新冠病毒,”梅林说,并补充说,“我们感到非常无助,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仍然不足以对抗这种病毒。” 劳拉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但第三波疫情是其中最艰难的。 “在第三波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年轻患者。在最初的几波疫情中,似乎很多老社区和养老院都受到了影响。这次更可怕的是,你看到20岁、30岁、40岁的患者被使用呼吸机插管治疗新冠肺炎……对我来说,治疗比我年轻的患者太可怕了。” 劳拉还有几周就要休产假了。 她在怀孕期间一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照顾重症病人。 填补她的职位将是一个挑战,因为重症护理护士供不应求。 “护理这些病人确实需要特殊的知识、技能和判断力,”亨伯河医院的重症护理护士贾斯汀·莫雷诺(Justin Moreno)解释说。 他在大流行开始时就开始了他的ICU护理生涯。 他说:“目睹多起死亡事件会让人精神上、情感上非常疲惫,甚至会让人感到沮丧,因为你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莫雷诺说,他看到他的同事们经历的倦怠,还有一些人已经离职。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看到一些员工的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 重症监护室负责人拉曼·赖(Raman Rai)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每个危重病人都需要“一对一的ICU护士比例”。 她指出,该部门从来没有足够的具有重症护理专业知识的护士。 赖说:“这次大流行明确地表明,为了管理病人的护理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方法。” “重症护理护士在为患者提供生命支持干预方面至关重要。他们受过专门训练的能够管理一个病人血液流动,察看他们的生命体征,也能够管理并能够和跨学科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了解病人的需要和能够监测病人的生命支持。” 医院已经重新部署了工作人员来帮助护士提供护理,但是在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人手都捉襟见肘。 安大略省注册护士协会首席执行官多丽丝·格林斯普林(Doris Grinspun)说:“安省是加拿大注册护士人数最少的省份,所以你当然不会指望有足够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现在你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她早就警告说,该省存在严重的护士短缺问题,而现在,在卫生危机中,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很明显,缺乏这种宝贵的医疗资源。 她说:“800张新床位乘以4张,4位护士负责一位需要专门护理的重症监护室病人……这样一来,你就会把其他病房里那些有能力帮助重症监护室护士的人都挤出来。” 格林斯彭说,她很担心医院和医务人员在第三波疫情浪潮中受到的影响。 她说:“我的心情在为战壕里的同事们感到"麻木"和为没有采取正确对待感到"愤怒"之间摇摆不定。” 她说:“我们要求安省(卫生)部长克莉丝汀·艾略特……我认为她还没有失去道德的指南针,并有能力理解目前形势的严重性,她能从现在开始接手新冠病毒档案,直到这场大流行结束。” 当梅林准备离开医院,专注于扩大她的家庭成员时,她缺席带来的影响将在重症监护病房感受到,因为这些重症监护病房在第三次疫情大流行期间成为了“爆发关注的中心”。 她说:“我们只是在重症监护室里踩水(treading water)……我们只是在处理,我们只是尽量处理好。” (Tom编译整理) ref: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3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