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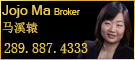 |
 |
 |
 |
 |
 |
 |
 |
 |
| 【本网讯】加拿大的护士表示,在COVID-19的Omicron变异疫情期间工作,使他们身心疲惫,针对医疗工作者的辱骂增加,已将他们推向崩溃的边缘。 根据《安大略疫情顾问小组》的一份报告,在疫情前,20%至40%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报告说自己严重疲劳。到2021年春季,比例已攀升至60%以上。 我们请多伦多的一位护士告诉我们典型的轮班是什么样子的。 利亚·罗斯瓦(Leah Rosevar)做了10年的护士,现在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工作。 这是一个关于一月份星期四夜班的故事,她告诉Ashleigh Stewart。 晚上7点:走进医院时,我把工作铭牌藏了起来 当我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时,我又累又晕。天已经黑了。 医院在我面前若隐若现;笨重的灰色团块建筑。只要一看到它,我就感到紧张、紧张和忧虑。 我昨晚又没睡好。我还做了另一个关于工作压力的梦——和2019年以来的梦一样。要么是我在重温那天的经历,要么就是一切都出了问题,我跟不上工作量。我有一次做噩梦的时候弄断了一颗牙。我从紧张性头痛中醒来。我在睡梦中听到铃声。 我开车去上班,因为这很容易,但现在也是为了安全。最近几周,同事们在公共场合受到的侮辱真的升级了。现在我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下车交停车费时,把工作铭牌藏起来,从后门进医院时,走路时低着头。如果我在晚上11点以后离开,我会让保安送我出去。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急诊室(ED)开始值班。像往常一样,一片混乱。一个男人在喊一些荒谬的东西。人们争论。有些人半戴着口罩,或者根本不戴。 晚上7:30:我在一片混乱中开始我的轮班工作 我与另一位分诊护士会面,从白班的工作人员那里拿到报告;他们告诉我们候诊室里的人员情况以及谁应该被优先考虑。 人们经常轻视护士或认为我们不重要。但我是医疗行业的眼睛、耳朵和心脏。我接受了四年的培训,能够系统地评估和确定哪些病人“病情最严重”,需要首先就诊。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确保你得到最高标准的治疗。 今晚,我们少了两名护士,也就是说,根据医患比例规定,不能使用八张床位。这并不少见。 今晚候诊室人满为患,这几天一向如此。新冠肺炎对此做出了贡献,但这不是大多数人来这里的原因。许多人在有其他病因的情况下检测呈阳性。 Omicron在很多方面造成了医院的堵塞。越来越多的轻度病人进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已感染COVID,但也有更多真正严重的病人进来,因为他们因为担心在医院感染COVID而延误了治疗。术后并发症的数量也会增加,因为人们为腾出床位过早出院。 病人被困在走廊的担架上 今晚在候诊室,有一名男性患者胸痛需要紧急做心电图检查心脏活动;一名老年妇女摔倒了,可能髋部骨折,躺在走廊的一个滑动门旁的卸车担架上,每个病人都必须经过这个滑动门;一名有自杀想法的有精神方面疾病的病人和四名服用芬太尼过量而失去反应的病人。 由于医院没有可用的担架,而且所有的病人护理室都满了,后四名病人中的两名不得不和急救人员呆在一起。这不仅使急救人员无法回到路上去值班,而且他们的担架也非常狭窄和坚硬,所以这对病人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像这样的卸载延迟经常发生;病人有时要等几分钟,有时要等几个小时。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位60岁的老人在急救用担架上躺了6个小时,我们才给他弄到一张床。 还有大量其他“低风险”患者:3名腹部或胸痛的年轻健康患者,几例手指撕裂伤,一位有咳嗽/感冒症状的人需要使用COVID拭子,一些下肢受伤的人,一位头痛的人,1人有UTI症状,1人耳朵有异物,有几名怀孕早期患者出现阴道出血或妊娠并发症,还有几名无家可归或被赶出收容所。 这里就是医院的战场。 我每班都要面对辱骂和骚扰 登录电脑软件后,我开始给病人分类。 当患者来到医院时,会给他们问卷进行COVID筛查,但只有在他们入院时才会进行检测。我们试图用塑料隔板隔离病人,但在这么忙的时候几乎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这也让人们更加愤怒——我们会因为距离规定和不允许访客进入而被骂。 我今晚试着筛查的病人中有一半要么没做成功要么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由于医院正在施工,我们的急诊科也被分成了一楼和十七楼,以弥补我们失去的空间。这让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 晚上9点30分,一个病人来到服务台,问他还要等多久。我试图解释,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有多少不同的因素影响这一点。他的反应是对我大吼大叫,告诉我他已经等了54分钟了,他的家庭医生当时让他“马上”去看急诊。 以前当人们像这样对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很害怕,特别是当你看到情况升级的迹象的时候。但最近,这变得很常见,我每次轮班都会被被辱骂。人们有时会说我太年轻,有时会对我发表性别歧视的评论,有时会叫我b-ch -(婊子)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的很多同事都遭到过种族侮辱。今晚早些时候,我的一个同事被骂"回到船上去"。 医院管理人员不得不把生命体征监测仪固定安装在墙上,因为人们总是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扔向我们。 有一次我在精神健康科(mental health unit)值班,我受到的最严重的侮辱是一个病人对我说,让我去死,说我很无聊。那是我工作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 晚上10点:人们不断涌入,但没有空余位置了 晚上10点,急救中心的主管给我打电话,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有多个病人被医护人员推迟卸下,救护车因此也无法再上路值班。但是急诊科已经堵满了——仍然有大量的病人进来,还有几个人需要心脏监护,这就需要特殊的病床和专科护士。没有任何可以安顿病人的地方。 那个摔倒的老妇人还在走廊的担架上等着。医生已经对她进行了评估,并安排了止痛药和照x光,但还没有提供药物。因为等候区的病人不能被密切监护,所以我们不能给病人麻醉剂。 这位女士需要上厕所,但又下不了床。我们不能用便盆,因为候诊室里无法保证隐私。 有一间复苏室是免费的,本来是给病情最严重的病人用的,但因为病床太短,我们经常在这种时候用它们。 我们决定把她转移到那里,但就在我们准备的时候,电话响了,告诉我们有一个病人需要紧急护理。髋部骨折的女人必须待在走廊里。 在这样的时刻,我感到内疚和失败。我知道她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我不能给她。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是道德上痛苦。 急诊病人是一名年轻男子,被发现在市中心昏倒了,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很快被分诊,送进了急救室。由于他不能睁开眼睛或按指令说话,而且对疼痛刺激没有反应,几名护士和一名医生不得不协助,使得其他护理区域缺少了这几位被指定的护士。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夜班员工已经回家了,这使得我们的人手更加短缺。我现在一个人在分诊。 候诊室仍然坐满了人。 凌晨1点:警察来了 由于缺乏工作人员,以及复苏室需要更多的资源,现在急诊科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一名在候诊室担架上昏倒的药物(毒品)滥用患者已经站起来,稳步走向洗手间,这意味着他现在可以被转移到椅子上或自愿离开——腾出一张床。但他无处可去。他说,收容所没有床位,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留下来在医院过夜,第二天早上社会工作人员就会来看他们。 刚过晚上11点半,髋骨骨折患者的房间终于空出来了。到了这个阶段,她已经尿湿身了。她很尴尬,并为自己成为“负担”而道歉。我想帮她清理一下但我得回去分诊了。 被这样对待一点也不体面。作为护士,我们也承受着这种压力。我们知道病人应该得到更好的治疗,但资源有限,我们真诚地在尽力做到最好。 现在是凌晨1点,也就是事情变得非常疯狂的时候。我轮班快6个小时了,还没有休息一下。 过去两小时内,我们有六辆救护车抵达,大部分送来的都是滥用药物或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我们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让他们单独在医院,所以现在警察也在等候室驻守。在他们的监护下,一个病人有自杀的风险,另一个则有杀人倾向,正被克制住,但还会大喊脏话。 疲惫的病人把烦恼发泄在护士身上 几个病人终于有了床位,现在可以转移到住院病房,但接待护士正在休息,所以急诊科一直堵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空间得到释放,但工作负载不会因为人员问题而减慢。这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 一些病人在等待超声波成像结果(一晚三家医院只有一处有超声波人员)或等待放射科医生读取图像。还有很多病人在等其他专科的会诊,比如妇科,但唯一的妇科医生在楼上接生,所以这些病人要等上几个小时。他们累了,饿了,不舒服,他们把他们的沮丧发泄到护士身上。我们试着让他们保持冷静,但他们的负面评论却没有停止。 到凌晨2点,候诊室里挤满了无处可去的无家可归的病人,他们试图用轻微的抱怨来逃避寒冷,还有那些有药物滥用问题的人,他们的睡眠几乎过度。 还有一些严重不适的病人仍在等待治疗,还有一位病人正处于精神健康危机的阵痛之中。一些病人开始互相争吵,需要保安介入。一个病人砰的一声关上了急诊科洗手间的门,把门从铰链上撞了下来,跑出了急诊室。 凌晨3点:休息室里“满是蟑螂和老鼠”。 我终于在凌晨3点休息了。在12小时的轮班中,我们应该有两个休息时间(一个45分钟有薪休息,一个45分钟无薪休息),但我们倾向于一次休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轻松一些。 我拿着一盒剩菜进了休息室。这个房间真恶心——到处都是蟑螂和老鼠,温度从来没有超过17度,所以我们都在里面穿夹克。 我感到疲倦、紧张和脱水。我的耳朵上有个人防护装备(PPE)造成的溃疡,而且因为整天戴口罩,我长了严重的痤疮。我是悲惨的;身心俱疲。 我太紧张了,无法睡个小觉,脑子里不停地想着我所有的病人,试图回想起我是否遗漏了什么。 我休息完回来,把一名受到性骚扰的护士领到我们之前分诊过的受害者的房间。通常这个时候,候诊室会安静得多。但现在由于寒冷、新冠疫情以及庇护所缺少床位,这里整晚都变得很忙。 白色警报:病人袭击医生 早上5点,我听到了喊叫声。一名患者被发给了一份1号表格,这意味着医生认为病人需要接受精神病科的评估,不能私自离开。病人很生气,正在威胁医生。然后她推了他的胸部。医生跌跌撞撞地回退了几步,但仍能站立。 其中一名员工按下了他们的紧急按钮(我们都被要求携带一个),一个白色警报就被触发了。保安前来护送病人到一个房间。护士们试图在医生给病人开药方的时候让情况缓和下来。 再说一遍,我对这种情况不再害怕。我对这种事已经不敏感了,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但这在情感上很痛苦,因为感觉太没必要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力资源,我们就可以对病人进行足够的监控,以防止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 现在是早上6点。是时候重新评估那些在候诊室睡了一夜的无家可归的病人了。我们给他们公交车代币,有几个人不想离开。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必须护送他们离开医院。 一名病人因此变得很暴力,在被扶到门口时对保安拳打脚踢。另一个白色警报被触发,更多的保安来护送他离开医院。 早上7:30:下班了,我想辞职 早上七点半,在为一位从床上摔下来的老年病人进行分诊后,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向即将到来的分诊接班报告了情况,我已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脸上满是个人防护装备留下的红印子。 我都等不及要回家睡觉了。但12小时后我又得回来再做一遍,这让我很痛苦。我们的排班是两个白班,两个夜班,然后休息五天。听起来好像有很多休息时间,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从一周的创伤中恢复。 我每天都想辞职。我喜欢护理,我只是讨厌它现在的样子。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情感拉锯战。 护理是一种职业。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护士需要多年的训练、技能培训和实践。我这么努力才来到这里,我终于对我的技能有了信心。 但新冠疫情暴露了安大略省医疗体系的脆弱性,该体系正在崩溃。 持续的护理短缺意味着额外的压力源,加上疫情大流行,危及患者安全和护理标准。 当人们喜欢我们的时候,鼓掌和敲锣打鼓是很好的,但“最真诚的感谢是不会付账单的”。他们不包括工作中经历的创伤。 我去年的实得工资约为52,000元。我的大多数护士朋友都有第二份工作。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感到身心疲惫。压力和我们一起回家。它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医护是一项团队工作,由于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切实际的医护要求,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受伤或辞职,而现在,又因为保护人们的安全而被指责辱骂。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非常内疚。我觉得我让公众失望了。我不能为人们提供应有的照顾,这让我没有满足感;像一个失败者。 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多做事,不要要求太多。但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没有什么多余的可给予了。 (Tom编译整理)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3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