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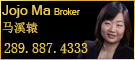 |
 |
 |
 |
 |
 |
 |
 |
 |
我一开始就错了。 阿富汗的住宿信息在网上很匮乏,我却想着傻人有傻福,等抵达喀布尔后再寻住处。在喀布尔机场漫天要价的司机堆里,我选了一位看起来最敦实的司机,叫他载我去市中心找住的地方。 他一副“我听懂了”的模样,却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把“市中心”听成了“大酒店”。 我被载至一家名为“繁星”、装饰豪华的酒店门前,由于不愿住在这里,司机又开始向我不断推荐另一家名为 “阿里旅舍”的旅馆,顺势还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我左手握着手机,冲着话筒里阿里旅舍的人嚷嚷:“我说了,我不住,不住!”右手则不断拍司机的座位靠枕,喊着:“我要去的是市中心,不是大酒店!” 电话那头的人操着浓重的阿拉伯口音,急促地说:“50美元很便宜了!你找不到更便宜的了!你必须住这里!” 他的用词太咄咄逼人,我厌恶地按断通话,气鼓鼓地把手机递给司机,质问道:“我说要去市中心,你却载到繁星酒店!我说了不去阿里旅舍,你还给他们打电话!” 2 然而,车停在繁星酒店的门口,司机怎么也不肯再发动车子了。 他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要么在他推荐的阿里旅舍住,要么住这家繁星酒店,如果还不行,那就自己走路去找。 就在我们俩僵持之际,繁星酒店的前台侍应走了出来,他好言劝我先进去看看房,不满意再换别家也不迟。就算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侍应还是坚持着,笑容甚至傻得有点动人。我想着自己就进去看看,心里盘算着如何佯装不满意。 繁星酒店有两扇防弹大门,门口配置着金属探测仪,还有几位背荷枪实弹的保安——阿国境势动荡,自杀式袭击频密弄得到处风声鹤唳,住在这样的酒店自然相对安全,可价格不便宜。 单人间最低90美元一晚,侍应看我听了价格之后表情木楞,补充道:“给你特殊优惠,只要50美元。”当时已近黄昏,我揽过背包坚持要走,侍应扯住我的手臂不让,“喀布尔入夜后非常危险,当地人都不敢独自步行,更别说你一个外国女性了。” “等等!”他一个机灵跑回前台,给老板拨了电话,一番对话后把话筒递给我。 “你来阿富汗干什么?”电话那头传来了老板的声音。“旅行”,说起自己刚毕业,我不自主地嘟囔道:“就是穷学生才没钱住酒店嘛!” 不料,老板说:“20美元,收你20美元一天,求你住下来,哪怕一天也好。”我恬不知耻地小声回应:“20美元还是贵……” “如果你愿意,可以住一晚,明天再动身找别的住宿。”老板建议道。 门外天色已黑,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就住了下来,末了还不忘掷下豪言,“我只住一晚,明天就搬。” 事实却并非如此——第二天我又接连问了好几家旅舍,发现条件最差的都要价50美元,并且安保系统还不齐全——远不如这家“繁星”。
3 第三天入夜,前台致电,说老板想和我“聊聊”。夜里10点约谈,动机难免让人起疑,但又想着人家减免我房费,我把防狼喷雾往牛仔裤后袋一塞便走下楼去。 寒暄过后,老板告诉我:“繁星酒店里还住了一些中国客人,你也明白,我们这里最低的房价是90美元,我们和他们的公司有长期合同,所以优惠一些,每天收他们80美元。” 我点点头,他接着说,“有中国工程师听说了你的房价,到我这里来投诉。”我一愣,什么? “我是生意人,此事一旦外传,我的生意难做。”他说完这番话,我这才想起,曾有中国工程师在酒店门外与我聊天,问及房价,我如实告知,不曾想他们也住在繁星酒店。 见我窘迫,老板忙说没关系,又问我这几天在哪儿用餐。 繁星酒店供应的自助餐16美元一顿,我只能每天在外面就餐。可由于语言不通,再加上是“外国女性”的敏感身份,我在穆斯林餐厅里点餐的经历并不顺利。 还没来得及说,老板就拍板发话了:“明天起,你一日三餐都在酒店吃,我已经交代员工不收你钱了。” 如果说优惠房价是老板体谅我是个穷学生,那免除饭钱,便显得不简单了。我开始猜疑这背后的用心——毕竟生意人不会做赔本买卖。 他接着说:“其实我和你搭乘同一趟航班,从迪拜飞喀布尔。我是阿富汗人,但有英国国籍,长居伦敦。前台侍应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顶层,从你入门开始的一举一动,我都透过监控镜头看在眼里。”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借故身体不适就回了房间。 第二天出门时,前台伺应转话:“老板说今晚想找你聊天。”我推搪自己今天会晚归,需要休息,聊天不便。 果然,第二天傍晚,我还是收到了老板的短信,“甜心,我等你回来聊天,多晚都等。回来后给我打电话。”亲昵的语气一改之前聊天时的严肃。 我只好尽力绕过监控摄像头,一路鬼鬼祟祟地溜回房间,不再出来。次日一大早就退了房,准备前往阿富汗东部城市赫拉特。 4 在去赫拉特之前,我曾向在喀布尔的朋友问询建议。一位阿籍记者力劝,“赫拉特不如喀布尔安全,只要走出市中心区域,极易被塔利班绑架。而且你在赫拉特搭乘车辆,司机也会打电话给塔利班,叫他们来绑架你。” 另一位阿国摄影师说得更骇人:“到了赫拉特,一定要打起精神,紧盯出租车司机载往的方向——往左,是死亡之路,通向塔利班基地;往右,那才是去往赫拉特城区。” 这句话让我坐上赫拉特出租车后,一直惴惴不安。我紧盯前方,生怕司机一个左转,把我送去塔利班巢穴。 老天保佑,赫拉特热闹的城区渐现眼前。 我住进了一家叫“马可波罗”的旅馆,最便宜的单间要价30美元,我随服务生进房一看,发现摆了两张床,怕弄错了,便又问了一次房价是多少。 “矿泉水就快送来了,每间房供有两瓶免费矿泉水。” 服务生回答。 “不是,我问房价是多少。” “贵?不贵!马可波罗的房价算很便宜了。” 我无奈,“我问的是这间房多少钱。” 他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伸手去开冰箱,说:“的确是不冷,冰箱可能坏了。” 我有些崩溃,提高了音量:“我问的是房价多少!” 他转身,探头进卫生间,转头说:“有水的!” 我无奈得瘫坐在床上,拍着被套说:“你连冰箱、矿泉水这样的单词都会说,就是听不懂一句‘多少钱’呐!” 他摆摆手,叫我等等。过了五分钟,他用一个大托盘,给我端来了20瓶冰冻矿泉水…… 我不再问了。 5 照着赫拉特城区地图,我一路走到了赫拉特古堡。买门票时被告知,参观时间只剩下半小时。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说若是我不介意,他可以陪我逛古堡,且能延后关门。 这个管理人员叫“郝马欧”,是古堡旅游区的主管,一路用流畅英文介绍古堡历史。我猜测他可能是想收我导游费,就在这时,他让我在原地等,很快又和另一位工作人员一起回来。 郝马欧说,“若和你单独相处,容易惹人非议,把另一位管理人员叫来,就能镇住人们好事的嘴。” 郝马欧告诉我,在赫拉特旅行很不安全,他决定第二天开车载我去参观其他景点。的确,自从进入阿国后,我在街上步行往往受到各种干扰:有时是人们跟着我,语言轻佻带着侮辱;有时被孩子们追着要钱,只要不给张嘴就骂;有时车子靠路边停下,人们开窗朝我吹口哨、尖叫;有时是警察把我拦下,叫来出租车把我送上车…… 那天,古堡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直把我送到酒店门口才放心离开。想起他们提醒我,在赫拉特应该用大块的布料包裹全身,我便决定自己步行去找布料店。 找布料店的路上有个看似正经的男子跟我搭讪,“你去哪里?”我不理会,男子又说:“你一个人走不安全。”我还是不理会。 男子不再说话,就一路跟着我。这时,一辆摩托车驶过,无意钩到了我的背包,男子冲上前,一把帮我拽回了背包。见他帮我,我忙道谢。 他随我到了布料店,见我和老板沟通不了,就帮我翻译。我买好了裹身的布匹,准备回酒店,男子问,“去哪里?”答说回酒店。男子说,“一起回。” 我火冒三丈,让他离开,他不仅不走,还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从包里摸出电击棒,推开电源,电击棒发出“啪啪”的声响。他不仅不怕,还哈哈大笑,“你哪弄来的?” 万幸,一辆载客三轮车刚好经过,我跳上了车。 6 第二日,郝马欧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来酒店接我,带我游览了清真寺,正午时分,他俩要回古堡工作,便把我交托给另一位朋友哈利。 哈利邀我去他家做客,去见见他善良的妈妈。 事实也的确如此——哈利妈妈皮肤白皙,一双深邃大眼似渊深湖泊。她只会达利语,与我沟通不来,端来的水果和饼干却是一盘接一盘。 我左手捏一块姜糖饼,右手握一个不知名果子,左一口右一口,还不忘喝一口刚调好的奶茶。也不管她听懂没,连连惊呼好吃。哈利妈妈看得开心,忽然像想到了什么,转身进房,捧出了一把银饰。 这连忙摆手说不要,哈利妈妈以为我嫌少,又进屋拿出了首饰盒子,取出一枚银戒指。这礼我受不起,哈利妈妈急了,扯一把哈利,让他说话。 “银饰不贵,但年代久远,每一串每一枚都有故事,既然妈妈一番心意,就收下吧。” 哈利说。我不好意思,于是挑了一条款式最简单的手链和一枚最小的戒指收下了。 初抵阿富汗,不懂官方语言达利语,简直是寸步难行。于是,我学了些简单词汇:“Salaam”是你好,“Tashnob”是厕所,“Tashakor”是谢谢。 我想致谢,又想着哈利妈妈不懂英文,于是就想卖弄一下自己的达利语。我看着哈利妈妈,握着她的手,深情地,笑盈盈地说:“Tashnob(厕所)”。 哈利妈妈已经做好被感谢的准备了,听了我的话,她一时愣住,恍了会神,就指向一扇门。 “你妈妈怎么了,我说的是Tashakor(谢谢),为什么她指着房门?”我问哈利。他听罢,“扑哧”大笑起来。 从那天起,我就用红笔在左手手背写下:“Tashakor,谢谢”,每天睡前描一次红,生怕褪色。 7 从赫拉特再回喀布尔,我又面临住宿难题。无意间在飞机杂志上看到一则旅馆广告,对方承诺每天房费只收25美元,便决定前往。 搭乘出租车前往,车却越走越偏远,就连司机都说,“一个女孩子住那么偏远很危险的!”——是啊,何况那是阿国。 于是我让司机推荐住宿,不料,他却说,“阿里旅舍”。顿时,我就回想起那通不愉快的电话。别无选择,再加上司机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转头、带着亲切的笑意说,“我和阿里旅舍的人很熟,会叫他们给你优惠的。”我便同意了。 阿里旅舍远比我想象中要好,门口有荷枪保安,房间整洁,服务生是清一色、约莫20出头的大男孩们。 入住后才知道,阿里旅舍的老板也很年轻,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俄语专业,准备到俄罗斯念书。 后来,青年老板不断向我解释说,自己以前英文还不错,学了俄文后,就把英文都忘光了。我这才明白,他那天在电话里话语急促、用词不妥,不是不友好,而是拉拢客人心切又比较紧张。 每天经过大堂,都可以看到青年老板愁眉苦脸地监察一楼餐厅的施工情况。他告诉我,阿里旅舍统共有30间客房,但最多时也仅有十间住人。旅舍占地面积大、水电开支不小,每月租金折合人民币(专题)近2万元,“旅舍一直在亏本营业。” 渐渐地,我们越来越熟悉。 我每天出门前都要和旅舍里的每一位服务生打个招呼,回来后也要和他们聊聊一天的见闻。尽管有时候他们听不懂,但依旧会坚持听我说完。他们希望每一位来阿国旅行的人没有被骚扰、没有经历不快。 但实际上,好的坏的我都经历过。 我每天披着头巾、衣着密实地走在街上,还是被不少阿人当成妓女,挑衅的语言甚至是过分的动作都会不时出现,甚至有小孩驾着驴车,经过我面前,把手在脖子前一横,做出割喉的动作。 但这些不快,我都没告诉阿里旅舍的人。 一开始,旅舍的服务生们给我的早餐是一大碗牛奶燕麦、一块馕饼和一个煎鸡蛋。渐渐地,份量愈加惊人,变成了一碗燕麦、两大块馕饼、两个煎鸡蛋、一壶绿茶和一杯热奶茶,还有数盒黄油和果酱。 这也是一种敛着呈现的恩情吧。 8 每天入夜后,旅舍门前都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在兜售丝巾。 阿富汗的街头孩童大多是因贫辍学,有些孩子就靠卖一些小首饰赚生活费,若是客人不买,便骂骂咧咧。更多的,选择了伸手乞讨,我不想让他们学会不劳而获,于是就曾被一大群小孩追着辱骂。 相较之下,阿里旅舍门前的围巾小孩则显得非常讨喜,他总是一副温顺模样,些微低着头,对着傍晚归去的我轻声问:“女士你好,请问你今天要买围巾吗?”他每晚问一次,我的心就软一次,可我真的不需要围巾,也不想因为同情去买。 一天,我想起自己背包里还有一大包国内的手机挂饰、钥匙扣等小礼物。于是整一包拿给阿里旅舍的前台,让他们转送给围巾小孩,说是送他的中国礼物。 第二天夜里,我回得很晚,喀布尔入夜后的气温低得叫我环住手臂。围巾小孩还在旅舍门前,他衣衫单薄地站在围巾架子后面,孤零零地望着漆黑街道,盼着人来。 我礼貌性地问他吃饭了没,小孩仍是那温顺惹人怜的表情,低头小声说:“女士,我还没吃,我很饿,可是得卖完围巾才能回家吃饭。”心头又一软,我走进阿里旅舍,问前台可否帮我叫一份披萨外卖。 “Carrie,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前台大男孩说。 “是想给门外卖围巾的小孩的。”我说。 听我这么说,前台大男孩回头跟里屋的青年老板聊了几句,继而转头对我说:“Carrie,这不是你的事,不需你操心。” 我以为他是怪我多事了。 几位大男孩随后就进了厨房。没多久,端出咖喱鸡块、两大块馕饼、一盘水果、一碗米饭和一壶热茶,端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继而端出门去。见我呆住,青年老板才说:“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负责门口小孩的每顿饭。” 这才醒悟,那一句“不关你的事”只是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英文表达。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不住地点头。 9 在阿国将近一个月,父母盼我早点回家。离开前夜,我向阿里旅舍的每一位员工道别。大男孩们窃窃私语,一致说,“你应该给家里带一些纪念品的。” 纷繁的战火摧毁了阿富汗的工商业,这个国家从零食到生活用品,都来自世界各国。本土可做纪念品的无非是干果、珠宝和手工毯子这寥寥数样。“阿富汗干果可是出了名的好吃,可以给家人带一些。”大男孩们告诉我。 到了市场一看标价,干果折合人民币近一百五十元一包。我看着青年老板,希望他能告诉我这种干果味道一般,好让我不买,不料他却说:“阿富汗的干果,可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事后证明,这个“全世界最好吃”的评价真的毫不夸张。 想着家里的大小亲戚,我咬咬牙多拿了几包,想起阿里旅舍里的每个人,便对青年老板说,“明天我离开前,想给大家做一顿中餐。”于是又挑了些中餐食材。 结帐时,我掏出钱,青年老板却怎么都不肯让我付账,“你是阿里旅舍里每一个人的朋友,我们不能让朋友出钱。” 不知道怎么报答,在离开的这天,我一早起床,砍鸡块、切蔬菜、调酱料、烧开水,给阿里旅舍的朋友们做了一顿勉强凑合的中餐。离航班起飞还有两个小时,想起通往机场路上还有层层安检,菜没来得及试味,我就要退宿付账了。 阿里旅舍的前台男孩眉眼满含着笑意,瞥了一眼青年老板,对我说,“想要退宿,先问老板。”我只好看向青年老板,他淡淡地说:“不用付钱。” “什么?” “你不用给钱。”他又重复一遍。 我的眼泪忍不住开始打转,心里着急,不希望善良的人做亏本生意。 “真的不用给钱,你做的这顿饭就当作是住宿费了。这些,无关生意,关乎情谊。” 眼看赶航班的时间不多,我执拗不过。同阿里旅舍的每一位大男孩告别后,坐上他们帮我叫来的计程车前往机场。 10 靠近机场的路上,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搜身检查,携带的大包小包既要过金属探测仪,又要打开被人工再检查一次。 好不容易进入机场,又要面临层层安检。先是进入暗房,被阿富汗女人摸全身,然后随身背包被打开,私密袋子也被拉开细细地查;再过金属探测仪。我的相机包通过时,金属探测仪时响了,安检人员态度很不好:“里面有电筒!” “相机包里哪来电筒?”我回答。他把相机包朝安检台上使劲一摔,说:“我说有就有,打开!” 登机时间迫近、路上安检恼人,他态度粗鲁,我一下子就来气了。我一把夺过相机包,取出相机,把相机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倒在桌上,还嫌不够解气,又扯过随身包,把物品“哗啦”全倒在桌上,吼道:“查!我像恐怖分子吗?我是游客,有必要这样查验吗?” 他瞥我一眼,“游客?不可能!”这一瞥看得我很是无奈,待他查完,只得一样样拾回物品,胡乱塞回包里,身旁安检人员也过来,默默地帮我收拾。 五分钟后,坐在候机室,回想起自己的行为,又回想起这些天自己经历的种种,我的脸却涨红了——我怎能这样?既然心甘情愿来到阿富汗,就应对阿国的安全状况有所了解,加上一路对袭击、绑架、爆炸事件的耳闻,更应该理解和尊重阿富汗小至餐馆超市大至机场安保措施如此严密的意义所在。 我起身跑回安检台,对刚才那位安检人员道歉。他没听懂,我又找来一位乘客帮我翻译:“我应该尊重你们的工作,我知道阿富汗不安全,你们的检查虽麻烦,但也是为保障乘客安全,这其中包括我。我对自己刚才的无知粗鲁行为表示歉意。对不起!” 负责翻译的乘客的达利语一说完,所有人都笑了。这位乘客对我翻译说:“他们也想对你说对不起,刚才他们太凶了。” 回到候机室,我给爸爸发短信:“爸爸,我住的旅舍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在我离开时还不肯收我的钱,我感动得有点想哭。” 爸爸的短信回得很快:“女儿,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样的好人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别轻易落泪。” 离开阿富汗前,我不带遗憾。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3 Comsenz Inc.